霍天云真是非常好,在谷飞霞脆弱的时候,没有要她坚强,而是理解她的情绪,还真是暖男所为。
霍天云不是没有自我,而是不去刻意显示自我。
但是他适应环境起来,那是游刃有余。
在什么点上,该怎么表现,他基本没有出过错。
那么跟他越是长久交往,就越觉得舒服。
这种人有积蕴,有底气,能够走近就是福气。
当然他也不刻意结交朋友。
平时也不会显山露水,他本身也像字画一样,需要静静地品赏。
没有静气,根本走不近他的。
原文是—— 想起无相上人
霍天云轻轻念这首诗:
“汲井漱寒齿,清心拂尘服。
闲持贝叶书,步出东斋读。
真源了无取,妄迹世所逐。
遗言冀可冥,缮性何由熟。
道人庭宇静,苔色连深竹。
日出雾露余,青松如膏沐。
淡然离言说,悟悦心自足。”
这首诗用现代语言迻译,意思就是:
“汲起井水来洗漱过寒冷的牙齿,又定了心神拂去衣上的尘埃;我在闲散的时间中拿一本佛经,走到东斋外面诵读。佛经中的真正道理,人们一点都学不到,而妄诞的事迹,却反而为世俗所徵逐。佛经中遗留下来的名言,我固然能夠有所领会,说到修养性灵,又岂是容易成功的呢?道人的庭院里很清静,青苔的颜色接连着深深的绿竹。太阳出来还剩有一点雾露,我见到这种景色,觉得淡然的境界,不是言语所能道出,一种了悟和欢喜的心情,已经感到满足便了。”(此处根据沈云亭“精校唐诗三百首”注释。)
念完了这首诗,霍天云赞道:“柳子厚(宗元)这首诗写得真好,这是真正‘悟道’之语。你看‘真源了无取,妄迹世所逐’这两句,把一般舍本逐末的所谓佛门弟子讥讽得好惨。‘淡然离言说,悟悦心自足。’和陶诗的‘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’意境相通,可说得是当真到达了‘不落言诠’的禅定境界。”
他滔滔不绝的谈诗,其实是用心良苦,是希望转移谷飞霞的哀思的。谷飞霞也不知有没有听见他的议论,好像仍然沉浸在回忆之中,呆呆的看着她父亲的遗墨。
霍天云又道:“子厚诗常在出世语中有入世语,例如这首诗就和一般诗人与方外之交的酬唱不同。但妙悟佛理的境界却是更高。你爹爹写这首诗送给无相上人,想必这位无相上人也是一位有道的高僧了?”说到此处,忽地好像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情,问谷飞霞道:“你爹和这位无相上人的交情怎样?你可知道这位上人是不是也懂得武功的?”
谷飞霞瞿然一省,说道:“你问这个干嘛?”
霍天云道:“你刚才说在广元没有相识的亲友,要是这位无相上人尚未圆寂,他是你爹爹的朋友,不也算得是你的相识的上辈吗?”
小时候看梁羽生的书,很喜欢其中诗词的引用,而且他好像也知道是小朋友在看,所以尽量让孩子们看懂。
比如说《冰川天女传》里有《诗经》的引用,现代对《诗经》是有所隔膜的,毕竟不大用的。
于是行文中不但有原文,还有译文,而且译文也很美,不是每一个作者都能写得出来的。
看来是梁羽生精心挑选,要不就是他所钟意的,那么品质自然不一样。
柳宗元的这首诗知道的人不多,但是霍天云看上去是了解颇多的,他是信手拈来,任意挥洒得在点评。
书念得少的,还真接不上话了。
难怪他平时话不多的,也不喜欢过分显露。
那是把心思浪费在美丽的,有价值的事物上,这样自然提升的审美鉴赏力。
从霍天云读到并点评的这首诗来看,“真源了无取,妄迹世所逐”,这还真是醒世之言,现在都适用。
真正的道理,有用的东西都是朴实无华,可能人家看都不要看。
可胡说八道,胡作妄为的却趋之若鹜。
这也符合《黄帝内经》所说的人总是“以妄为常”。
同时也在说,谷飞霞的担心和烦恼也是“妄念”,她并未了解真谛。
话是对的。
可身在烦恼中的谷飞霞肯定听不进去,她能听一听就很好了。
霍天云的心灵能量很强大,他其实不明就里,谷飞霞也不会全然告知,只会流露出一鳞半爪,碎片化的信息。
但是他通了,当然也不会明说,到底是人家的事,人家的隐私。
不过随意引申和发挥,却万变不离其宗,一语中的。
这是他心灵能量强大,引来的灵感,而且灵感只是一部分,还不是重要的。
重要的是他的灵性已经开启,他本来就有基础,具备灵慧,经历世事,让他灵根聪慧,花枝具实。那么接下来会如何呢?敬请继续观赏。
--END--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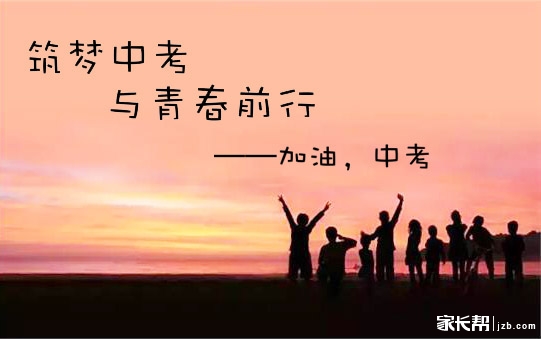


看过了,登录分享一下感受
或留下意见、建议吧~